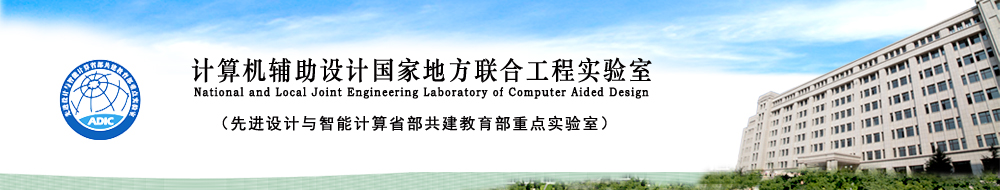2001年4月,有人在太原市某古旧市场倒卖旧版军用地图,安全部门追根溯源,查到个体书商刘智奇。8月17日,刘因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逮捕。他交代,80多张制作于“文革”期间的军用地图是从另一书商处连带许多古旧书籍一起收来的,而后者是从测绘局搬家时处理、出售的废品中发现的。
2002年1月15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是否泄密成为案件焦点。刘智奇觉得他因收藏过期军用地图而坐牢很冤枉,而军方的鉴定结论是:上述军事地形与目前部队使用的军事地形图相一致,所标密级没有发生变化,仍属重要军事秘密。辩护律师则认为,涉案的是军事地形图版本,而不是军事地形。地图版本的出版、作废、解密有一定的时间,而军事地形在一定时间内是不会变的,以“地形和地形图”相一致,得出“仍属国家秘密”的结论缺乏说服力。本案最终没有对被告是否泄密作出结论,作为公诉机关的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撤诉了——2002年1月31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这一结果,刘智奇6个月的监禁生活得以结束。
慎用手中的权力
这些曾经发生的案例,提醒我们严肃认真地对待密级鉴定工作,慎用法律赋予的权力,考虑到当前的司法实践,这一点尤其突出。上文所举的两个案例,因为不涉及敏感问题(比如外交斗争)或其他因素,总体上相对简单,仍不免给当事人造成极大困扰,而搜索多年来累积的案例,因结论不当引发争议乃至造成被动的例子虽然不多,但其影响不可等闲视之。
西方国家把司法最终裁决视作一条基本的法治原则,其前提是政治体制上的三权分立,我国不是这种情况。套用西方概念和标准来衡量密级鉴定的法律定位及效力,把它当作一种行政裁决来分析与司法裁决的关系并主张后者的终局性,无法做到理论上的圆融,在对照现实时又有难以克服的矛盾。
现实的情况是,保密法明确把密级鉴定权授予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其权威性不容置疑。但是权力大责任也大,使用不当,好事有可能变成坏事。如果有独立司法做最后一道防线,行政部门的错误或不足还有弥补、改正的机会,从而避免造成损害当事人权利的后果。但是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司法系统比以往更倾向于尊重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的判断,罕有密级鉴定结论不被法院采纳的消息见诸报端。这可以解释为相关工作日渐成熟、完善,密级鉴定已达到极高的准确率,但为鉴定者考虑,为当事人权益计,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慎重对待手中的权力。
隐私权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我国1987年实行的《民法通则》以及1988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没有规定隐私权这一公民的人格权,只有名誉权一说。直到《妇女权益保护法》才第一次把隐私权引进普通法律的法条中来,紧接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使用了隐私这个词语。